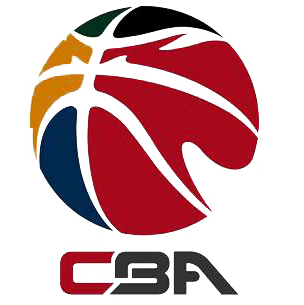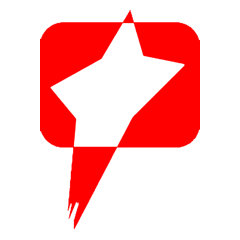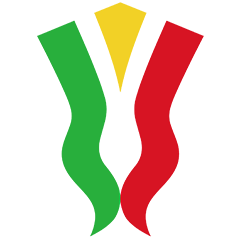文︱陸棄
近日,曾被戲稱為“流動的下水道”的塞納河,首次向公眾正式開放游泳。這一刻,媒體興奮地將其定義為“歷史性勝利”,而巴黎市政廳則將其包裝成綠色治理與環境修復的典范。然而,在慶祝的浪潮之下,必須有人追問:這一切的代價究竟是誰在承擔?當城市用奧運會來檢驗生態修復,它追求的究竟是可持續的環境,還是一場面向全球直播的公共關系秀?

塞納河的“清潔工程”背后,是高達15億歐元的財政投入,是數十年城市下水系統的翻修,是大量農業、工業污染源的強制整治。這些看似令人肅然起敬的數字,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構成了“生態治理的特權樣本”——因為只有像巴黎這樣被全球關注的城市,才可能在國際賽事的壓力下獲得如此大規模的資金傾斜和行政動員力。而對于法國其他城市甚至歐盟內外的大多數城市來說,哪怕是一個河道消除氮磷污染的預算,都是無法承受之重。
人們確實在慶祝塞納河的“再生”,但這個“再生”究竟是一次治理范式的轉型,還是一次為奧運形象粉飾的表演性工程?答案并不樂觀。美聯社與法國本地媒體均指出,塞納河的水質依然存在不確定性——雨季突發降雨會導致細菌含量暴漲,河道中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依舊滯后。甚至連參與水質監測的技術公司都承認,現行的檢測手段無法在“實際時間尺度上”反映真實的微生物污染程度。換言之,公眾在“清澈”的河水中暢游,可能只是在一場技術數據優化的幻覺中自我陶醉。
更荒誕的是,巴黎當局決定效仿“海灘”設置紅綠旗的方式來實時通報水質。這種方法本身當然可以理解為對安全負責的機制安排,但它的象征意味卻令人不安:在一條常年流經首都、貫穿多個居民區的河流中設置“開放時段”,仿佛是一種對公眾空間片段化、項目化管理的極端體現。這是對城市公共性的一次重構:自然空間不再天然屬于市民,而是根據“可消費性”來切割分配的資源。市民在這一過程中不再是權利主體,而是“游客式用戶”。

這背后當然有全球大賽的壓力在推動。巴黎奧組委早在2017年就承諾,將在2024奧運前徹底清潔塞納河,并在此舉辦鐵人三項與馬拉松游泳。這一承諾在當時被許多人視為不切實際,甚至是笑談——而今,政績目標倒是完成了,但執行邏輯依然是典型的“為比賽而治理”:臨時性、集中性、高成本。這種治理模型并沒有解決生態治理的系統性難題,反而更像是一場環境整容手術,用最短的時間掩蓋最深層的問題。
與此同時,歐洲當前面臨的政治氣候,也讓“塞納河奇跡”的光環更加復雜。歐洲議會右翼勢力上升,法國國內抗議不斷,馬克龍政府陷入“民眾遠離—精英孤島”的治理危機。在此背景下,將塞納河作為“治理典范”大加宣傳,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對外表態、對內動員的雙重符號。環保、公共健康、科技治理,這些曾屬于全球綠色轉型的話語,如今也成了國家形象工程的一部分。
而真正令人警惕的,是這種“奧運式治理范式”的可復制性問題。塞納河之所以能被清理,不是因為法國政府突然對水質格外上心,而是因為有一個無法延期、全球直播的賽事“卡著節點”。這就讓環保工作與政治表演產生了危險的共生關系——只有當它成為一項可交易的政治項目、可展示的國際承諾時,才會被真正落實。這不僅扭曲了環保工作的本義,也制造出一種“只對鏡頭負責”的治理幻覺。

有趣的是,就在塞納河“盛大開放”的新聞被刷屏的同時,歐盟內部卻因水資源危機而持續告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新報告指出,全球近四分之三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地正在遭受“水太多”或“水太少”的雙重威脅。在這個生態危機前所未有加劇的時代,塞納河清澈的水面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只是一個精心打磨的櫥窗:美麗、昂貴、脆弱。
而在櫥窗之外,還有太多河流正在被遺忘、被犧牲。法國國內,盧瓦爾河、羅訥河等多條水體依舊面臨著水溫上升、物種銳減、農業面源污染等長期威脅;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萊茵河、意大利的波河也在氣候變化下頻繁出現枯水斷流。對這些河流的治理并沒有奧運項目的催化劑,也很少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它們是“無聲的河流”,卻更真實地反映著當下生態治理的失衡現實。
這就是今天的悖論:我們在為一條河的“復活”鼓掌,卻忽略了它可能只是一場治理光環下的偶然奇跡,而非全局勝利。塞納河不是問題的終點,而是質問的起點。在全球生態治理碎片化的今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是哪條河流的顏色,而是我們對治理目標、公共資源分配方式、環境權利邏輯的理解。如果只有奧運會才能換來一條清澈的河,那么問題的根源,就不是河,而是制度。

 精品閱讀
精品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