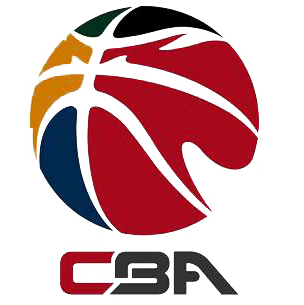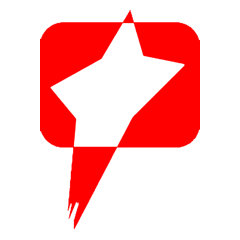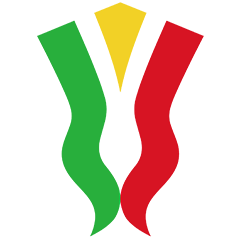2025溫網首輪,3號種子茲維列夫時隔六年再遭大滿貫一輪游。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德國名將首輪爆冷出局后的一番話,遠比比賽結果更令人揪心:“我有時會感覺很孤獨。我的精神狀態很差...做任何事都缺乏快樂。”這不是一個運動員關于技戰術的檢討,而是一個年輕人對生活意義的迷茫告白。

茲維列夫的困境折射出職業網球殘酷的一面。這項運動將青少年時期的天才們早早推上職業舞臺,給予他們掌聲、金錢與光環,卻很少教會他們如何處理隨之而來的孤獨與壓力。當茲維列夫坦言“即使贏球時也感受不到快樂”,當西西帕斯首輪退賽后暗示可能考慮退役,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代球員的集體低迷,更是職業體育體系下個體心靈的困境。這些年輕人從小被訓練如何擊球、如何跑位,卻很少有人教他們如何在勝利后不迷失,在失敗時不崩潰。

90后球員群體確實面臨著特殊的歷史困境。他們成長于三巨頭(費德勒、納達爾、德約科維奇)的陰影之下,當終于等到巨頭們老去時,卻發現阿爾卡拉斯、辛納等更年輕一代已經迎頭趕上。梅德韋杰夫、西西帕斯、茲維列夫這一代成了夾縫中的一代,既無法像前輩那樣開創王朝,也不像后輩那樣擁有無限可能。這種“歷史中間物”的處境,無形中加重了他們的心理負擔。

職業網球的全球巡回賽制本質上是反人性的。球員們每年有近40周漂泊在外,住著不同的酒店,身處不同的時區,身邊只有教練團隊這個小圈子,疫情時期的隔離政策更加劇了這種孤獨。當茲維列夫說“感覺生活中很孤獨”時,他道出了巡回賽中許多球員的共同感受。網球是一項個人運動,但并不意味著運動員就該承受如此沉重的心理代價。

茲維列夫考慮尋求心理治療的表態是一個積極的信號。長期以來,職業體育界對心理問題的污名化使許多運動員不敢公開談論自己的困擾。事實上,頂尖運動員的心理健康問題遠比公眾想象得普遍。從大阪直美到茲維列夫,越來越多球員開始打破沉默,這或許能推動職業網球體系建立更完善的心理支持系統。

當我們談論90后球員難成大器時,或許應該反思我們對成功的定義是否過于狹隘。在一個產生過費德勒、納達爾、德約科維奇這樣傳奇人物的時代,評判標準被扭曲了。不是每個優秀球員都必須贏得大滿貫,正如不是每個優秀作家都必須獲得諾貝爾獎一樣。茲維列夫們已經達到了絕大多數職業球員難以企及的高度,他們的價值不應僅僅由冠軍數量衡量。

茲維列夫的孤獨告白提醒我們,在關注比賽勝負之外,更應該看到運動員作為人的一面。當網球不再給球員帶來快樂,或許整個體系都需要反思:我們是否把太多期望壓在了一些年輕人肩上?在追求精彩比賽的同時,我們是否忽視了那些創造精彩的人的心理需求?

體育的本質是人的活動,而人需要的不只是勝利和掌聲,還有理解與共鳴。也許,當職業網球學會更好地照顧球員的心靈時,我們才能看到更持久、更健康的精彩表現。在那之前,讓我們給予這些敢于袒露脆弱的球員多一些寬容——他們不僅在為自己的職業生涯而戰,也在為我們共同的人性而戰。(來源:網球之家 作者:Mei )

 精品閱讀
精品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