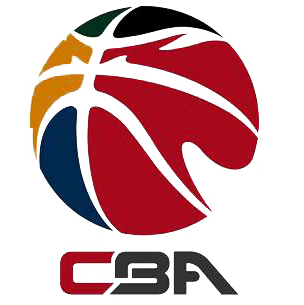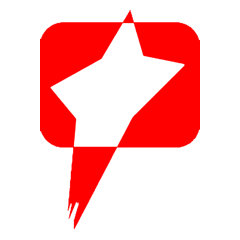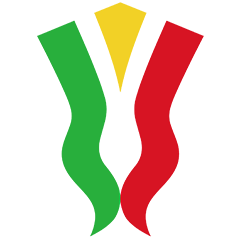2025年3月30日,來自湖北省宜昌市下轄一個縣級市枝江市的女選手趙靜(化名)站在枝江市“逐夢芳華”女子半馬的起點,她身邊,熙熙攘攘簇擁著8000名女跑者,她們都在興奮地等待著發令槍的聲音。
在這一道枝江最美的風景線里,有很多湖北跑者熟悉的身影:省內小有名氣的精英選手王麗、“松滋一姐”李婷、多次拿下馬拉松和越野賽冠軍的項英……包括趙靜本人,也在朝著半馬125的精英成績沖擊。
她的腦海里,閃過了四年前那場在枝江舉辦的“長江超級半程馬拉松”的場景,那是她的家鄉第一次舉辦馬拉松賽事,而正是這場賽事,讓枝江這一座長江邊的小縣城開始蓬勃著馬拉松的激情:參加跑步的人群尤其是女性越來越多,多到可以舉辦一場純女子賽事的程度;報名極其火爆,8000個名額當天就爆滿;為了滿足女性跑者的需求,時政甚至專門為她們改建了場地、增加了硬件設施。
四年前一場半馬賽事的種子,終于在2025年開花結果了。而澆灌這一株花果的,就是枝江縣城那些通過跑步,找到自己人生救贖的女性們。

用腳步掙來的家庭話語權
比賽在家鄉舉行時,趙靜(化名)對馬拉松幾乎一無所知,只當是政府組織的某項活動。她原本和同事相約前去“湊熱鬧”,卻因加班爽約。她并不知道,那是枝江歷史上首次萬人馬拉松,更不曾料到,自己會在不久后踏上跑馬之路,并終將以所向披靡的姿態站在隊伍最前方。
錯過了那場枝江馬拉松后,趙靜在兩年后的2023年4月30日,以1小時38分的成績完成了人生首場半馬,并奪得市民獎。這份驚喜點燃了她內心的火種。她開始系統訓練,想看看自己究竟能跑到什么程度。跑步逐漸占據了她幾乎全部的閑暇時間,隨之而來的,是丈夫與婆婆的質疑:“不顧家”“不是個好母親、好妻子”。
一邊是不斷進步的配速和數據帶來的成就感——“原來我也可以這么厲害”的自我認同令人著迷;一邊是來自家庭的冷眼和不解,這讓她感到焦慮、孤獨。她時常陷入自我懷疑:“這樣真的值得嗎?”“女人到底還是該以家庭為重吧?”
然而,跑步帶來的身心愉悅與掌控感,終究令她難以割舍。為了平衡跑步與家庭,趙靜將訓練時間壓縮到極致,同時在家務上更加勤勉,也盡量將賽事地點選在省內或周邊縣市,裝備能省則省。每逢比賽臨近,她便提前半個月“好好表現”——訓練多在清晨進行,若需跑長距離,原本5點起床的她會將鬧鐘撥早一小時,不敢開燈,躡手躡腳起身,在黑暗中備好早飯,收拾好孩子的書包和校服,只為爭取短暫的訓練自由。


凌晨四點的江邊以及晨跑的趙靜
趙靜通過馬拉松拿到手的獎金越來越多。一開始是幾百,后來慢慢變成幾千。2024年遠安半馬,她以130的成績站臺,獎金數額甚至超過了丈夫當月的津貼。

2024宜城半馬,
趙靜再次將自己的PB成績刷新至刷新至126
“跑步真能掙錢?”丈夫和婆婆一臉難以置信。
“是啊,只要足夠快。”趙靜笑笑。
婆婆裝作不經意地瞥了一眼趙靜手機銀行的余額,嘴里念叨著“跑得快能當飯吃?”卻順手接過了她手里的臟衣籃。
“你明天還要訓練吧?那我送孩子去上舞蹈課。”丈夫低頭收拾餐桌,語氣中少了幾分抵觸。
“我這個愛好幾乎沒花過自己的錢,這就是我堅持下去的底氣。”趙靜說。兩年來,她小心翼翼地在跑步與家庭之間尋找平衡,從沒想過,真正撬動家庭話語權的,竟會是那一筆筆不斷累積的賽事獎金。以2024年為例,她共參加了6場省內馬拉松,平均每場報名加交通食宿約250元,全年投入不到2000元,而獎金收入累計已達1萬元,遠超開支。
不知從何時起,她的訓練不再為家庭日程讓位;婆婆和丈夫也不再念叨“女人就該顧家”“曬得這么黑像什么樣子”。她第一次,在“母親”“妻子”“兒媳婦”的身份之外,以“跑者趙靜”的標簽獨立呈現。

一枚獎牌的象征性分量
對于本地人項英(化名)來說,那是一場改變命運的首馬。之前她最遠只跑過15公里,“并且是跌跌撞撞完成的”。回想起那時的場景,她說:“當時我對配速和裝備都沒有概念,只知道跑,去賽場的公交車上,幾位穿健康跑(5公里)衣服的女孩子在說我,‘看看這是跑半馬的,好厲害哦!’我聽了心里美滋滋的。特別有成就感。”
接下來幾年里,項英輾轉省內各種馬拉松和越野賽事。她發現,一枚閃閃發光的獎牌,足以讓她在嘈雜的縣城菜市場,換來一瞬間的尊重。
2024年某場越野賽中,項英拔得頭籌,除了獎金,還獲得了當地一家贊助商的青睞。那天,她一直沒舍得摘下獎牌。回酒店的路上,她穿行在一條被攤販擠滿的小巷,不小心蹭到一位大爺。大爺原本面露不悅,但仔細打量她一眼,立刻側身讓道:“喲,冠軍?厲害!”——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共空間里,僅憑“跑者”的身份,而非“誰誰的媳婦”“誰誰的媽媽”,贏得了陌生人發自內心的贊賞。


項英在越野中找到了暫時的自由以及快樂
奪冠后,她和獎杯、獎牌以及贊助獎鞋合了影
曾經走樣的身材、覺得除了“伺候”老公孩子外別無所長的自我懷疑,在一塊塊獎牌和一筆筆日益豐厚的獎金里成為過去。項英找到了新的自我價值和生活意義,而在她背起行囊外出參賽時,再無人用不以為然的眼光看她。曾經對她“占用家務時間訓練、跑得一身傷回家”冷言冷語的丈夫,也逐漸閉上了嘴。比賽地點近些的時候,丈夫和孩子甚至會捧著鮮花,在終點線等待她沖線的那一刻。
“我也不往遠處跑,省內的就挺好。一張火車票幾十塊錢,要是那邊有親戚朋友,就直接住他們家,大家人情往來也方便。”她說,“現在穿的裝備幾乎都是比賽得的,鞋是贊助商送的,這身衣服標價一千五。我覺得特別劃算,這愛好一點兒都不‘敗家’。”

一腳泥濘,卻是項英在越野賽中的見證
但在縣城,選擇跑步,并不只是消費決策那么簡單。
相比北上廣更為松散的家庭結構,縣城女性往往被包裹在自己和婆家的親屬網絡中,面對的遠不止職場壓力,更有復雜的人際關系、親戚的層層意見和隱形的道德審判。一旦將馬拉松當成主要愛好,意味著不僅會出現家庭之外的支出,還會被質疑對家務的投入不足。
“報名費、交通、住宿,一場比賽下來怎么也要一千元。”一位女性跑者坦言,“這還不算平時的裝備開銷。一雙好點兒的跑鞋四位數起步,一雙哪兒夠?還有冬天戶外跑用的外套、壓縮衣褲……對不跑步的人來說,這事兒完全不可理喻:明明馬路上就能跑,為啥要花錢?”
單從付出和回報是否能成正比上看,馬拉松的確會令這群縣城女性跑者陷入自證陷阱。然而,馬拉松給予她們的回饋,早已超出了字面意義上的“付出”和“回報”。

洶涌的運動欲與跑馬潮
2021年的枝江半馬,在許多普通女性跑者的記憶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彼時,來自松滋的銀行職員李婷(化名)首次參賽是為了緩解壓力,她在幾個月前跟著同事開始跑步,本是“玩一玩”的心態,卻漸漸上了癮。枝江距離松滋不遠,她便帶著父母和孩子一起來“體驗一下”,并不在意成績,只想感受一次馬拉松的氛圍。
而王麗則在不久前的宜昌完成了首馬。她來自湖北山區,跑齡不過兩年,聽說枝江賽道平坦,便想著趁機測試一下自己的半馬水平。她低估了小縣城的對馬拉松熱情——人聲鼎沸,她甚至沒聽清發令槍響。剛一抬腿,她便被四周喧騰的聲浪打亂了節奏。直到賽道過半,她才在這股浩浩蕩蕩的人流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步伐。


日常,冒雪訓練中的李婷(左)和在高校跑步的王麗(右)
這場長江超級馬拉松,像一枚深水炸彈,悄然在流經這座小城的江面上掀起漣漪。黑人選手的一騎絕塵、萬人奔踏的聲浪、女子冠軍伍玲捧杯時的笑容……讓站在賽道上的她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激動與共鳴。那一刻,一個聲音在她們心中響起——“原來普通人的腳,也能踩出回響。”

那場比賽的女性參賽者雖然不足900人,但她們帶來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賽事層面上,它讓枝江市政意識到了逐漸蓬勃的女性運動市場,也催生了后來的“逐夢芳華”女子半馬;民間意義上,女性跑者在枝江受到的重視程度,隨著人數增多而逐漸強化。2021年舉辦馬拉松后,枝江新增了6處社區夜跑燈帶,女廁位實現倍增,這一切都在表明,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在朝著有著運動需求的女性傾斜。



枝江沿江大道燈火通明的夜及禮化路的燈帶
四年后,專為枝江女性跑者量身打造的2025“逐夢芳華”女子半馬應運而生。 賽道上也出現了很多熟悉的面孔:王麗已成為省內小有名氣的精英選手;李婷是當仁不讓的“松滋一姐”;項英拿到了一項項馬拉松和越野賽的冠軍;曾經不知馬拉松為何物的趙靜,正在向半馬125沖擊。
起跑線上,趙靜與項英穿上配色講究的戰袍,淡妝登場:“誰說打扮漂亮就是招搖?我們要穿裙子,也要涂口紅,要美美地站上領獎臺。”

趙靜(中)一 馬當先跑在 前列
2025年枝江女子半馬,專屬女跑者們的狂歡盛宴
訓練場邊,李婷帶著兒子揮汗如雨:“誰說男孩只能父親帶?跟著媽媽,照樣能練出一身肌肉!”
學期末,王麗向學生發出邀請:“誰說老師只能板著臉?來,和跑馬拉松的老師組隊,沖線去!”


李婷帶兒子跑步(左)
王麗帶學生拉練(右)
枝江文旅局副局長魯作龍表示:“縣城女性被壓抑的運動需求,比想象中更洶涌。”

她們在跑道上做回自己
晚上10點,宜都城區的一家飯館剛剛打烊。55歲的老板娘張桂芬(化名)拉下鋁合金卷閘門。
“又去跑步啊?”
“是啊!”
“一個門面都不夠你折騰的。”
她沒答話,只是換上跑鞋,跑進空寂的街道。
“為孩子、為老伴操心了大半輩子,現在孩子成家了,老伴也走了——跑步讓我覺得,我第一次是為自己而活。”
白天,張桂芬是這家小店的老板娘
晚上,張桂芬是這條街最颯的大女人
在宜昌醫院當護工的劉霞(化名),平日里為老人翻身擦洗,腰酸背痛。可一到周末,她就雷打不動地出現在郊外山坡上,進行爬坡訓練:“伺候人是工作,跑起來才是給自己充電。”

再過半小時,
這條下班的路就將成為劉霞的跑道
剛剛離婚的陳雯(化名),曾被前夫冷嘲:“離了我你還能干什么?”半年后,她在成都馬拉松的終點線上張開雙臂,發布了一條朋友圈:“42.195公里我都跑下來了,還有什么路不敢走?”

跑完2020年10月29日成都馬拉松
陳雯用一條朋友圈記錄了自己的“新生”
“娜拉出走以后,會怎樣?”
這個被討論過無數次的問題,在縣城的跑道上有了答案:不必遠走,跑一場馬拉松就夠了。
曾經,人們眼中的縣城女性,生活半徑有限,或圍著家庭打轉,或投身小生意與基層事務,忙碌卻不被看見。她們的活動范圍局限在縣域與鄉鎮之間,“外面的世界”似乎離她們很遠。她們的個人需求和自我實現,在這種語境下被湮沒。她們承擔著家庭的主要責任,并被蓋上“沒見識”的標簽。
然而,當馬拉松的賽道從都市延伸到縣城,站在賽道起點的她們,從羞怯走向自信,從附屬走向獨立。在“母親”“妻子”“女兒”之外,她們為自己爭取了“跑者”這一嶄新而有力的身份標簽。這個標簽,給予她們更廣闊的精神空間——她們的身體不再只是“適合生育的工具”,她們的存在意義,也不再以照料丈夫與子女為邊界。
今年六月,某縣城跑團舉辦端午熱跑活動,組織者原計劃設置“最美孕媽跑者”環節,卻遭跑團女性成員的集體抵制:“孕媽不是噱頭,請叫出我們的名字!”最終,跑團決定在活動結束后,給每位參與的女性跑者一束花,附言:“為自己而跑,為自己驕傲。”

活動結束后的加油花束
她們未必深入思考過這種抵制背后的理論意義,只是出于一種樸素直覺:她們想以“自己”的身份站上賽道,而不是作為某人的“妻子”或“母親”。她們就是自己,一個個有著鮮活思想、蓬勃軀體、燦爛笑容的人。如今,“離異帶娃”“最美娃媽”這類稱謂漸漸淡出人們的話語體系,取而代之的,是“跑團一姐”“越野女神”這樣因能力和堅持而來的新稱呼。

樸素有力的縣城女性主義
這場由下至上的“縣城女性主義”,無聲卻有力。她們用腳步在生活的戰場上為自己“步步為營”地爭奪生活中的自由一隅。
跑步,不再是“不務正業”;訓練,不再被視為“作為母親和妻子的失職”。跑步讓她們找回自信,也讓她們意識到,生活并非一眼望穿的死水,而是一條可以憑自己劃出波紋的河流。跑步成為她們兌換家庭話語權的硬通貨,讓她們用汗水澆灌出樸素而堅韌的女性主義實踐——身體的覺醒、價值的重估、身份的再造、空間的爭奪,以及發生在廚房和客廳里微妙的權力變遷。
由于工作與生活的牽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可能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法到全球各地去跑“六大滿貫”,甚至連國內的大滿貫賽事都很難報上名。她們只能在省內或周邊縣市“隨便跑跑”,可這并不妨礙她們擁有一個值得驕傲的身份:跑者。從最初換上并不專業的運動裝備、在跑道上邁出第一步的那一刻起,她們就已經走在了那條自我實現之路上。起步即征程,無所謂遠近和快慢。
當都市女性在商場爭取母嬰室的“她空間”,當好萊塢明星為“MeToo”奔走疾呼——這些縣城女性,正用她們變黑脫落的趾甲,在腳下延展的賽道上,親手擦除那句無形的訓令:“女性應該是什么樣子。”
她們用實際行動回應:沒有任何樣子,是女性必須的。

枝江江邊晨跑的她們
六月,跑者陸續進入夏訓。頒獎臺的喧囂漸漸遠去,江邊的風帶著水汽拂來,天氣開始轉熱。
日子依舊是日子。她們仍是媽媽、妻子、女兒,依然在生活的軌道上運行。菜市場里的討價還價,接送孩子的等待,工作臺前的忙碌,灶臺邊的油煙,一樣不少。
但有些東西,確實已經不一樣了。
本條內容創作團隊
作者:張蕊
編輯:WR China Team/沈天浩
圖源:官方媒體/受訪者提供
投稿、應聘兼職作者,請聯系


 精品閱讀
精品閱讀